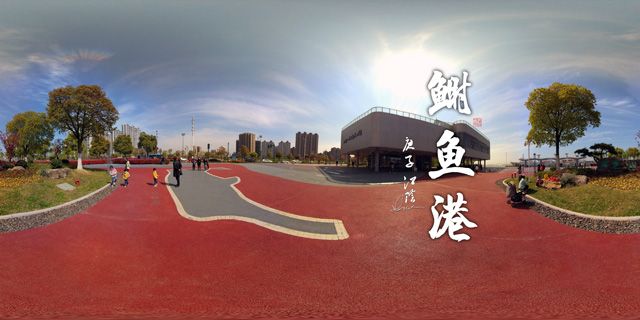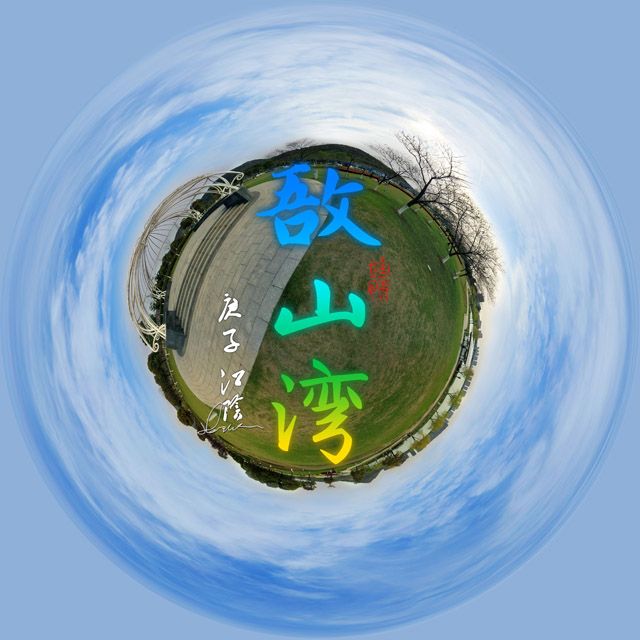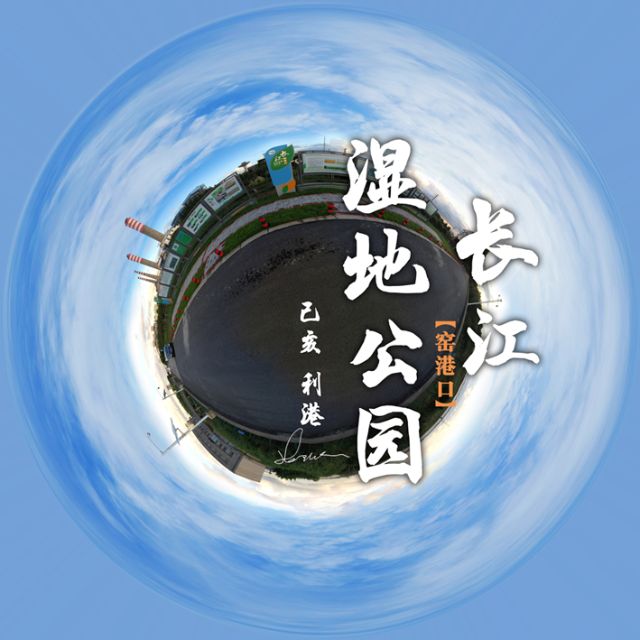子衿 本姓陶,江苏江阴人。农家子弟,书生本色,敏而好古,不慕荣利。爱读书,喜远足。闲暇常著文遣怀,颇称己意。
一个百岁老兵的抗战自述
(一)
我叫仰书鼎,今年98岁,对的,我今年98岁,虚年龄99啦!
我住在北大街光孝坊巷,江阴的北门地区。我家祖上是安徽的、徽商,明代时从安徽歙县来到了江阴,最后定居到了北门浮桥,做些小本买卖。我太公叫啥名字我不记得了,只晓得老辈人都喊他“仰大麻子”——他长着一脸的麻子,我家的底子就是由他打下来的。我太公有3个儿子,我爷爷是长子,叫仰桂林,他靠开茶叶店和酒店起家,慢慢实力大了,就开了家“鸿昌”煤炭公司;后来又开了“仰源泰船行”,买了船,跑起了长江运输,靠水吃水嘛!发家后,爷爷想从居住的北大街大巷口搬出来,嫌那太热闹。我奶奶的弟弟是风水先生,阴宅阳宅都看,他对我爷爷说,光孝坊巷不错,左寺古坊,南北还有两只水塘,是块宝地;爷爷便买下了光孝坊巷的一块空地,造了6间高敞的青砖大屋,还有2间侧厢。房子落地窗、木板壁,房梁都是整根白果树雕花的,造得相当气派;前后还有两个院子,很大,后面院子里种满了四季菜疏,前面的院子里呢,爷爷种了棵腊梅。爷爷在世的辰光,不冷不热的傍晚,他喜欢在树下喝喝酒、听听书,高兴了,还会拿出琵琶,拨弄一阵。100多年过去了,如今,腊梅盘根错节,一到冬天,就会开出满树绒绒的黄花儿,我的院子和房里年年香气扑鼻,好像爷爷一直在陪伴着我,从没离开过。

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的、很快活。谁知到了民国二十一年,发生了两件事,影响了我的生活。一件是日本人打到了上海,我爷爷的运输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另一件事情就是,那年的农历四月,我母亲在生第七个孩子时,难产死掉了。母亲断气时,我小妹妹还小,以为妈妈睡着了,要爬到她身上去吃奶。遭受这两大灾祸,一个国仇、一个家难,国家的平静被打破,我家的生活也跌入了狼狈之中。我是家中长子,面对突然的变故,当然要挑起生活的担子;学自然是上不成了,父亲把我送到了上海,先在钮扣厂、又到药厂,挣钱贴补家用。我上海有个小姑夫,叫魏宗相,与孔祥熙的儿子是大同大学的同学,在统税局工作。民国二十六年上,小姑夫为我在统税局查验所下面的一号巡船上谋了份内勤的差使。巡船停泊在苏州河上,我的工作就是检查过往船只有无税单,有就放行、没有,则连补带罚。应该说,这是份很不错的工作,收入也要比厂里多,我因此做得非常起劲。不料几个月后,到了8月,日本人又在上海跟国军干了起来—苏州河一带是主战场——炮弹在空中飞来飞去,还带着呼呼的声音,一落地,到处都是隆隆的惊雷;惊雷过后,四下里马上成为一片血红的火海,红红的火光腾空而起,把半爿天空都映得通红通红的;红红的天空里,到处都是滚滚的浓烟,烈焰吐着长长的火舌,活像一条条吐着红色信子的毒蛇,毒蛇疯狂地扭动身躯,跳着辣豁豁的舞蹈,接着,耳边又响起乒乒乓乓的爆豆子一样的声音;也不知过了多久,声音渐渐稀了下去,可不一会,减杀声却又猛地响了起来。

我哪见过这阵势啊,吓坏了,赶紧跟着小姑夫逃到了租界,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郊外——小姑夫的父亲是海军部军械处处长,在真如有幢洋楼。逃难中,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双棉鞋弄丢了,那是舅婆做给我过冬穿的——母亲去世后,舅婆住到了我家,照顾我们兄妹6人的生活。新棉鞋丢了,我心疼了好些日子,心里更加恨起了日本人,是它让我没有了新鞋子穿的。
上海是呒不办法再呆下去的了,只好回到了江阴,谁料日本人像知道我行踪似的,一路追了过来——当然,他们的目标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——于是一家人只得像其他的江阴人一样,拖儿带女、仓惶踏上逃难的路途。当时江阴沿江的所有船只,不光是海军的舰艇,就连商船、民用船,也统统被政府征用一空,用来凿沉江底,淤塞航道,阻止日本舰艇沿江西进,侵犯南京。爷爷的运输船当时已被征用,他多了个心眼,悄悄将一只稍微小些的船只藏进了江边芦苇丛中。爷爷有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,武进焦溪人,爷爷决定先带我们去焦溪一带避避风头。已是深秋季节,霜降也过了,天气已经很冷,稻子却还成片地竖在田里,没人理会。上船时,恰好下起了雨,我们几个孩子冷得牙齿打起了架。爷爷、奶奶、舅婆、父亲、二叔一家4口、我、姐、2个兄弟及一个妹妹,还有邻居蒋永昌一家3口、船工骆驼一家3口,一船19人坐的坐、蹲的蹲,一路可怜兮兮地向焦溪逃去。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,讲课的空档里,养了一只大狗,随粥便饭,形影不离。当骆驼撑起竹篙,船只慢慢离开码头的辰光,这畜牲不知从哪冒了出来,猛追几步,一声嚎叫,跳上了船,我到今朝还记得那只狗跳起时那优美的弧线型的身姿。

不知过了几天,船摇到了泗河口孟岸堂村。这里靠近焦溪,周围全是圩田,地势低,抬头低头,都是白茫茫的水面,分不清哪是航道、哪是岸线,一船人到了这里才松了口气,感觉日本人不大可能会来这里作孽的。
日本人是没有碰到,但却遇到了“游击队”。我们上岸租房住了个把月光景,就有几个“游击队员”找上了门,看到我家大小箱子好几只,便认定我们是有钱人,开口就要钞票,可把我们急坏了。二叔打听到宋仁杰在焦溪,赶紧请来做“中人”——宋仁杰是江阴北门人,当过侦稽队长,在澄常武地区有些影响——宋仁杰把“游击队员”请到茶馆,吃茶“讲情理”,摆平了这事。

“游击队”没敲成“竹杠”,不死心,时不时地来骚扰,我们惹不起麻烦,就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船上,派我看守。好不容易上了岸,又要重新回到船上,我心里很不高兴,但又没有办法,只能蹲在船上、随风飘荡。作孽啊,有时肚皮饿了,又错过了饭点,只好上岸拔些黄豆,找个背风的高地掘个洞,竖起两块砖头,砖头上搁一只蚌壳当锅子,再就地拾些枯枝落叶,点上火,煨点黄豆,垫垫饥。
第二年开春,局势慢慢平静,逃难在外的江阴人开始陆陆续续回家,我们也回到了江阴北门。回家一看,家里倒塌败落,只剩下个空壳了,所有的东西都被日本人烧的烧、抢的抢,一样也没有了,奶奶、舅婆到家后,眼泪直淌。过去北门地区是相当闹猛的,现在再看,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,店里的货物抢了个精光,板壁、铺门被卸一空,就连地上铺着的地板,也被撬了个兜底朝天。难民回来了,无家可归,个个眼泪簌落落——爷爷烧了几大锅粥,分给大家一起来吃——我听大人们说,日本人是从北门攻进江阴的。日本人进城后,从城门头到江滩头,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,仅黄田港口的煤炭码头上,就有上百人被残酷杀害,抛尸江中。我那时17岁,不懂多少国家大事,只晓得日本人是强盗,侵略我们,害得我们遭罪落难。

(二)
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,生活总要继续,就像我家屋后的那条长江一样,它总归是要向前流淌的。过了两年,父亲有个同事,叫沈松寿的,介绍我到县政府民政科去干了份文书工作;不久又调到了军法处做了书记员。军法处的隔壁就是公安局和看守所,公安局有个翻译叫梅炳书,一来二去的,我跟他们都混成了朋友。
是秋天的一个晚上吧,大姑夫缪燮章把我约到滨江茶楼,说有要紧事。大姑夫原先在南街开了家南货店,沦陷时毁于战火,之后他把南货店开到了祝塘街上。见面讲了番家常话后,大姑夫切入正题,要我为抗战做点事情。原来,大姑夫公开身份是南货店老板,但实际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,军统江苏站情报员,专门负责江阴方面的情报工作;他要我利用县政府工作的有利条件,收集情报,为抗战服务。接着,大姑夫又说起了日伪多么可恶,军统多么结棍。
我当然晓得日伪是可恶的,它害得我丢了新鞋子、又害得我逃难到乡下。可是,恨归恨,突然要我与它作对、搞情报,我一时还下不了决心;再说日伪那么凶残,我心里还是感到害怕的。大姑夫见我犹豫,也没勉强。

说到这,有必要讲讲“忠义救国军”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有部样板戏电影,叫《沙家浜》,风靡一时。看过的人肯定对电影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、还有那个参谋长刁德一印象深刻,他们就是“忠义救国军”的军官。但实际上,历史上的“忠救军”可不像《沙家浜》里所描写的那样。“忠救军”当然反共,但它更加抗日,它就是成份复杂了些,什么样的人都有,包括封建帮会等等,这也难怪,“忠救军”本来就是戴笠组建的一支杂牌武装嘛!像咱们周庄的一贯道组织,“忠救军”不照样把它吸纳了进去?而且,还闹出了蛮大的动静呢。事情是这样的,有天早上,周庄的50多个伪警察正在吃早饭呢,结果稀里糊涂地就被当地的“一贯道”分子给咔擦了;后来日本人报复,又把这些“一贯道”分子收拾了。“一贯道”中有个叫“小拆酷”的,常来县政府寻他老乡白相,跟我也很要好。那次日本人要剿杀周庄“一贯道”,我无意中是从梅翻译那知道了消息的,当时想告诉“小拆酷”,让他活条命,但是不晓得怎样通知,结果“小拆酷”和他的那些同伙就这样完蛋了。熟悉的朋友活生生地在自己眼前消失了,应该说,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。反来覆去想了几天后,我找到了大姑夫,表示愿意当军统情报员。大姑夫听罢,拍了拍我肩膀,把我介绍进了“忠救军”澄锡虞办事处,归郁锡如领导。郁锡如安排对我进行了上岗前的突击培训,无非是关于情报人员的心理素质和业务技能方面的内容。最后,郁锡如给我颁了委仼状,还发了张工作证,“镇反”时,都被我一把火烧掉了,形势紧张,怕啊!

我的情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,那么我是如何干情报工作的呢?其实说到底,很简单,就是利用工作之便。刚才不是说了嘛,我在军法处当书记员。应该说,两年书记员当下来,我跟县府上下已经混得很熟,尤其那个梅翻译,更是熟得不能再熟了,这为我获取情报带来了很大的便利。加入军统后,每当得到有价值的消息,我一般先综合分析,再作出判断,然后就用米汤把情报写在纸上,再把纸揉作一团,塞进自行车把手里(我把笼头作了加工处理),然后骑车赶往北大街闸桥,那儿有我们的地下交通站。顺便交待下,日本人占据江阴时期,江阴有5个城门进出,每个城门口都有日本人站岗,检查过往车辆及行人,我送情报走的是北门。出了北门,骑车到了交通站后,我把情报交给交通员,交通员立即赶往闸桥码头,坐上江阴到常熟的轮船。几小时后,船到东乡陆桥,交通员离船上岸,步行半小时左右到达祝塘交通站,把情报交给交通员。就这样,经过几道手续后,我的情报最终到了郁锡如的手里,他用碘酒在纸上涂抹后,情报内容就显露了出来。

事情就这么简单。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情报工作多么神秘、了不起,甚至波澜壮阔,那估计他是影视作品看多了,中了谍战片的毒了——情报工作没那么神奇和神圣的,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,可能那些重要岗位、那些大特务的感觉跟我不一样,当然啰,危险还是蛮危险的。
有没有啥记忆深刻的事情?有啊!上世纪四十年代,敌后抗战活跃,日伪加大了扫荡的力度。一次我跟梅翻译一起喝酒,他平常喝酒很爽气的,那次却一反常态,喝得有点保守,我知道他心里有事,又不能上来就问,就不停地劝酒,看喝得差不多了,就套他闲话。果然,梅翻译说近几天要对武进焦店的“忠救军”来一次扫荡,是武进、昆山、江阴三地日军的联合行动,要他随时待命,所以他喝酒也不定心。第二天一早,我把这一情报送到了交通站,交通站立即启用另一条紧急通道,把情报送了出去。焦店的“忠救军”有了准备,设下埋伏,一举歼灭了40多个日本兵,还活捉了他们的少佐田中新一呢!

对了,还有件重要的事情,更值得在这儿说说的。大概在民国三十二年吧,江阴发生了桩特大新闻,汪伪县长韦长征(音)被军统刺杀了。这事说起来跟我还有关系呢!因为情报就是我送出去的,可以说,没有我的情报,刺杀是不可能成功的!韦长征是长泾人,当时是江阴的伪县长,卖身投靠日本人,苛捐杂税、鱼肉乡民,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;但这个韦长征又很能干,开始军统想把他策发过来,为我所用,谁知这韦长征是块茅坑里的石头,又臭又硬,不听军统劝阻,继续为非作歹、祸害一方,没办法,军统准备暗下杀手、为民除害。除奸任务交给了澄锡虞办事处,郁锡如让我摸清韦长征的行动规律。
接到任务后,我开始有目的地接近韦长征,我说的是接近他周围的人。说来也巧,韦长征的秘书是同兴里人,姓何,跟我是北门老乡,喜欢喝酒、听评弹。我就投其所好,下了班经常请他到我爷爷开的酒店去喝酒,陪他一起听书,慢慢的,我们的话就多了起来。一次听完书走出书场——好像听的是《十美图》吧——何秘书意犹未尽,关照我接下来别忘了把书听全,回来好讲给他听,我听他话音,感觉他要出差,又不便直接打听,就故意说一起来听就是了,干嘛还要我听了再讲给你听啊。何秘书就说他过几天要跟韦县长去趟长泾。原来这韦长征是个孝子,有空时常回家看望母亲,正好前阵缉私队长章忠德来,说泾河边开了爿船餐厅,请韦县长去尝尝;这样韦长征就决定过几天回趟长泾,先看老娘、再吃船菜,顺便检查检查河道税征收情况。听到这一情况后,我不敢马虎,第二天就把情报送了出去。郁锡如掌握韦长征行踪后,马上与“忠救军”章晓光部取得联系。他们到泾河边侦察地形,又控制住船餐厅,并派两名士兵伪装成跑堂的服务员。到了那天晚上,韦长征与章忠德酒正喝得起劲呢,就听“呯呯”两声枪响,两人倒在了地上;埋伏在餐厅周围的“忠救军”听到枪声,马上冲了进去,几个卫兵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呢,就成了“忠救军”的俘虏,等到日伪军听到枪声赶来,哪里还有啥“忠救军”的影子。

成功刺杀了韦长征后,郁锡如和我都得到了嘉奖,我被任命为中尉情报组长。不久,重庆成立了中美合作所,我又去那儿的情报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。两年后,我当上了上尉情报参谋。
民国三十四年,抗战结束了,中国人民拚死拼活,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8年抗战,流血牺牲,终于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,总算可以歇口气、吃口定心饭,太太平平过日子了,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;可是,让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,抗战胜利后,我非但没有过上好日子,反而开始了人生的磨难。

(三)
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接收了江阴,不知道是不是打了招呼的缘故,我被推荐去黄田港检查所当所长。检查所嘛,顾名思义,就是对进出黄田港的船只、还有人货进行检查,这是个肥缺,很多人眼睛睁得滴溜圆,盯着呢!果然,最后所长的位置落到了王宽的手里,为啥?不为啥,因为他是方骥龄的寄儿子啊;方骥龄是谁?他是新任的国民党江阴县县长啊!
所长没当成,我心里憋屈透顶,像爬进了无数只小虫子,又像是吃进了一只秤砣:我冒着生命危险送情报时,你王宽在干什么?我非常愤懑,也看透了官场的黑暗。过了些日子,父亲对我说,爷爷年纪大了,想让你帮他一起料理料理生意。你就别吃公家饭了!我考虑了几天,也好,世道如此,再说我对做生意也蛮有兴趣。就这样,我在北门浮桥堍开了家“茂昌”渔行,招了3~4个伙计,前店后河,做起了长江鱼的生意,每天的交易量都在几石以上,生意做到上海、苏州、泰州等地呢!接着,我又开了家“信诚”报关行,帮进入黄田港的货船办理相关手续,赚取手续费;我与海关上的青年军关系很熟,所以,我报关行的生意也不错。

转眼就到了民国三十八年,解放军的炮声还没响那,浮桥的大火倒烧了起来。怎么回事呢?当时,在我的东边不远处,还开着另一家渔行,叫“沙万成”大渔行,不知道什么原因,这家渔行的一间房子里竟然堆了几枚炮弹。有个国民党士兵向渔行老板借钱,老板没肯答应,一下把这个兵痞子惹火了,就在夜里偷偷放了把火,火势蔓延,炮弹炸了起来,整个浮桥地区变成一片火海。浮桥是北门地区繁华的商业区,街道两边的老房子密密麻麻,都是砖木结构,哪经得起火烧啊?大火烧了2天,浮桥沿河的店家都被烧得精光,我的“茂昌”渔行当然也逃不过去。大火过后不多久,解放军渡江了。后来呢,我的报关行也不开了。再后来,大概1951年吧,经人介绍,我先到民政科、又到工商局、再到盐业公司,最后到了税务局,做起了文书、总务工作,吃起了公家饭。
新政权刚刚建立的辰光,社会上到处都是乱哄哄的,因此,新政府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,当然就是千方百计消灭异己、筑固政权了,这很自然、可以理解、甚至也非常正常!可有一点,就是苦了我们这些不尴不尬的人了,像我吧,当初进政府当差,说穿了,不过是为了过日子、混口饭吃;但话又说回来,虽然你不属旧政权的铁杆分子、死硬派,可毕竟也与它有着牵丝攀藤的关系啊!什么?送情报、参加了抗战?是啊,谁说不是呢?但是,你要知道,我参加的可是“忠救军”的抗战,不是新四军的抗战,不能说啊,说了有可能脑袋就掉啦!

我是打死也不敢说的。可是,李纪良却把我供了出来。这李纪良是我过去军法处工作时的同事,长寿人,跟我关系不错。他怕乡亲们说他在伪政府做事,是汉奸,平时宁愿住在我家,也不太愿意回去。住得时间长了,他好像觉察出了什么,我呢,见他思想与我比较接近,曾想发展他加入我们的队伍,可他胆小,始终没敢跨出这一步。后来他到上海去当了一名教师。“镇反”期间,广泛发动群众,各单位都有指标,全社会大抓反革命。李纪良就向组织密报,说仰书鼎曾经加入过“忠救军”,是军统特务。消息从上海传到江阴,公安如临大敌,找上门来,1954~1956年,我被强行管制,吃了2年家庭官司。1963年12月13日,我被正式逮捕;1964年2月,投入苏州西山监狱。西山是苏州太湖中最大的岛屿,四面环水,面积比江阴城还要大出许多。我服役的那个监狱面对太湖,对外挂了块牌子,叫做太湖采石公司,我在那吃了13年官司,到了1977年,我才结束刑期,回到北门老家。

监牢里的生活嘛,其实也没啥好说的,除了干活还是干活:放炮、采石、粉石、运输,从早到晚,没完没了。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,叫做劳动最光荣,其实那是骗人的,真要光荣的话,也就不会用它来惩罚人了。
(四)
我在西山监牢里的时候,隔壁牢房里关着的,是我的小阿叔仰汉初,说起他,江阴地面上也是赫赫有名的。我小阿叔精通医理,尤其对于妇科和伤寒类疾病,更有研究,人称“仰一帖”,意思是只要他一帖药下去,立即药到病除。“一打三反”运动期间,浮桥有个叫田荣培的医生向上告密,说我小阿叔收听美国之音——当时是敌台——小阿叔因为这个罪名被捕,最后判了8年徒刑,也被关到西山监狱开起了石矿,做苦力。我和小阿叔有次放风时无意中碰到,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,几年没见,小阿叔瘦掉了许多,身上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精神,要知道,他可是曾经的西郊地区的代理镇长,很有点大先生的派头的,唉!

我在西山吃官司的辰光,刚过不惑,到我出狱时,已经年过半百,将近花甲之年了。孔老夫子说过,五十而知天命,这话真的有道理的。我今年98岁、虚龄99了,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命了,真的,就算你再能、再有本事,也“缠”不过命的,好像孙悟空,再怎么腾云驾雾,你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的。拿我仰家来说吧,挨斗的挨斗、自杀的自杀,我爷爷的三个儿子,还有他们各自的后代,没有几个的曰子过得是太平的、如意的,现在回想起来,就是当初爷爷造屋时的墙门没有开好,这是我奶奶的弟弟亲口说的,他是风水先生。据说我家的房子造好后,我这位风水爷爷跑来一看,发觉南面人家的墙角正好冲着我家的院门,赶紧就将门稍微朝东偏了偏,又在门上按了个铜圈,平时家人进出改走西面的小门。后来又发现,那户人家的烟囱也对着我家的大门,就跟人家商量,加了个遮档;不料过不多久人家又反悔了,只好再将遮档撤掉,结果仰家子孙的苦头就来了。

我和我小阿叔,当然苦头吃得最足,剩下来还有我的兄弟,干脆吃苦头把命都吃没了。我兄弟叫仰书田,民国三十四年时,和邻居蒋伯荣一起,考进了青岛海军军官学校,学的是轮机专业,毕业后到了舰艇上工作。不久解放军胜利渡江,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,打算撤往台湾。我有个堂弟叫仰书明,就是我二阿叔的儿子,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上学,是中共地下党员,劝我兄弟别去台湾。我兄弟听从他的劝导,留在了上海——蒋伯荣去了台湾——“镇反”期间,有人揭发我兄弟当过国民党海军,是历史反革命,严刑拷打;我兄弟受不了这样的污辱摧残,就在1951年元宵节的夜里,跳进了黄浦江。我那时在盐业公司工作,曾给我兄弟写过一封信,询问他的情况,也不知他收到了没有?我兄弟投江后,我小妹去给他收了尸,那年他28岁,刚谈了个对象,还没结婚。

堂弟知道我兄弟投江的消息后,心里非常过意不去,感觉是他害死了我兄弟。堂弟后来在复旦大学当教授,专门研究日本教育和文学;再后来,被划成右派,文革中关进了牛棚,吃了不少苦头。
仰家子孙就这样,读书的读书、做生意的做生意,总之都在外面,最远的跑到了挪威、美国和日本,定居在了那里。我爷爷的3房子孙,现在就剩下我这个孤老头子,没有老婆、当然也不可能有子女,独自一人,孤零零地守着这6间老房子,直到老死。

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对象的,是我的隔房表妹,我爷爷妹妹的外孙女,双方大人作主,亲上加亲。她的父亲是牧师,上海滩上有些名气,我们还在教堂里办过订婚仪式!后来解放军围攻上海,她们一家去了香港,这事自然也就耽搁了。这之后,又是“镇反”、又是土改,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,哪还有心思谈婚论嫁啊?后来我吃了官司,终生大事也就彻底没了希望,想想也正常,谁愿意嫁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呢?
当然,我的晚年也不全是孤苦伶仃的。1995年,我的老邻居、也是老同学蒋伯荣,就是那年和我们家一起逃难的、后来又和我兄弟一起当了海军的那个蒋伯荣,回到了江阴老家。他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后,也是孤身一人,没有结婚——他认了个寄女儿。回来后,政府给了他1间房(当初有3间),他干脆住到了我家,和我作作伴。那个时候,江阴正在造大桥,我们经常去看。蒋伯荣很高兴,说他们当年在舰艇上时经常要进长江的。3年后,蒋伯荣去世,我给他在花山买了一小块墓地。这20年来,年年清明我都要去花山给他扫墓的;最近几年没力气了,跑不动了,就不去了。

老辈头里江阴的交通运输、还有人员往来啊,靠的都是长江。南来北往的货物、还有人员,都从北门进出,北门这一带是江阴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方,我祖宗有眼光,刚到江阴时就住到了这里。现在北门是不闹猛了,但还有那么多的老屋在,老街老巷在:北大街、君山巷、光孝坊巷啦,同兴里、缪家场、章家场,校场啦,还有君山庙、武庙,等等,看到它们,我心里就踏实、就高兴。大前年夏天的辰光,有个公益组织,我忘了叫啥名字了,在全国范围内寻访抗战老兵,不知怎么就找到了我。他们告诉我说,像我这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,他们在全国找到了5000多个,咱们江苏有200多,江阴就剩我1个了(我们参加抗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);他们还说,这5000多人中,像我这样没有生活来源的——现在政府发我800元低保了——有1000多个。他们每月发给这些困难老兵800元生活费,我也有的。每月到了规定的日期,他们就把钱打到我银行卡上,我去附近的银行一取就行了。

好了,啰啰嗦嗦,一讲就是这么多,年纪大啦,没办法!再讲几句结束吧,省得你们厌烦。是这样的,前阵子有天晩上我睡在床上,忽然听到有呼呼的声音,一会,像有什么东西摔到了地上,我想,作兴是爷爷来看我了。第二天起床一看,你猜是啥?原来是两扇木头长窗被风刮倒了,扒在院子里、玻璃碎了一地。邻居告诉我,是台风刮的、昨天夜里的台风很大很大。原来是台风啊,我耳朵聋,还以为是爷爷回来了呢!

爷爷当然是不会回来了,除非是在梦里,但是,爷爷的腊梅年年会开。过了中秋,就是寒露、霜降,立过了冬,小雪、大雪说到就到,接着就是腊月。每到这个时候,爷爷的腊梅就开了,一簇簇的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,开得满树都是,我好像又看到了爷爷在树下喝酒、听书、弹琵琶。腊梅真香啊,我的院子和房里都是腊梅香味,就好像是爷爷在我身边,从来也没离开过一样。

.
.
.
END
作者│子衿
来源│影秋斋 乡愁江阴